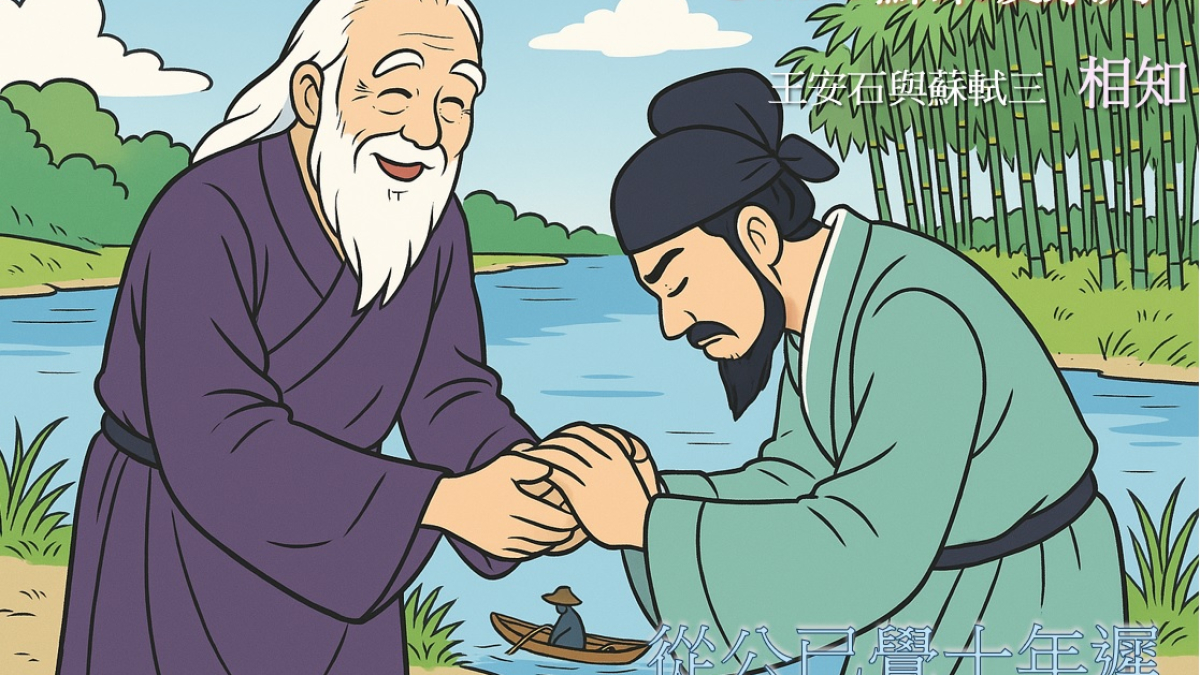王安石開始推行變法時,他是參知政事(副宰相),那時是熙寧二年(1069)。一年後,他升任宰相,48歲。而蘇軾是32歲,正在中央管理政府文件 [1]。兩人也是在壯年階段,十六年的差別,會造成很大的不同。不管是政治見解,人生體驗,都可以是南轅北轍的。更何況,那時候兩人都未曾經歷過真正的政治打擊,對世情,政情皆從非常自我的角度來作判斷。
十五年後,元豐七年(1084),這個差別就不再那麼重要了。他們倆都經歷了一次重大的政治打擊:一個是被同黨出賣過,兩度罷相,老來喪子的退休宰相;一個是被皇帝出賣了,九死一生,貶徙窮鄉的閒置犯官。就是這樣的年紀和際遇,已足夠讓他們知道,求同存異的重要。一個不再執拗,一個不再自傲,更能聽得到,聽得懂對方的說話。在江寧這個歷史名城中,他們再次相遇。
(三)蘇軾與王安石的相知
蘇軾和王安石達成諒解時,是元豐七年(1084, 蘇軾47歲,王安石63歲),地點是江寧(今日南京)。江寧之會是一則歷史佳話,也是一個歷史謎團。
據蘇軾的書信所言,他們倆在江寧只是遊山玩水,談詩論佛 [2]。其他方面兩人可能仍有分歧,詩詞佛理則可以各抒己見,無所謂對錯,也就成為了兩人的共同語言。真的只是這麼簡單,足足一個月,就只是談了這些?
原來,早在蘇軾與王安石見面之前,蘇軾收到「新黨」成員李琮的一封信。信中提到王安石十分讚賞蘇軾一篇《勝相院經藏記》,蘇軾回信自謙一番,並希望李琮轉告秦少游去跟王安石見個面 [3]。這明顯是王安石向蘇軾釋出的一個訊號;大家仍是有共同話題可以談談的。蘇軾亦心領神會;不然,當他得到神宗赦罪後,怎會貿然去見從前的政敵?若事前没有某種默契,那不是自討沒趣嗎?又,王安石為甚麼要放出這樣的訊息?
朱剛先生有如下的解釋:
「由此看來,王、蘇之間恐怕不是一般的和解,令人懷疑那已經不是撇開政治態度的詩酒之交,而是在政治上也已經獲得某種程度的互相諒解。」[4]
確實,蘇軾跟王安石告別之後,在江寧一帶尋找置業機會,但未有所獲。他仍是回信給王安石,表達了自己希望能與他成為鄰居,這樣就可以經常往來請教 [5]。除此之外,兩人也有詩歌答和,其中有句曰:「從君已覺十年遲」[6]。這一句詩的含意就是:早在十年前,能夠和宰相大人你合作的話,會有多好!十年前是甚麼時候?大約是熙寧七、八年間,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之後,再次回朝的那一段時期。這個時期有甚麼特別,以致到蘇軾想時光倒流回到那時?
或者我們可以如此推測:在江寧相會時,王安石向蘇軾透露了某些他想在十年前實行的計劃,在這些計劃中,他是預留了一個位置給蘇軾。真是如此的話,代表着王安石當年已經有同「舊黨」和解的打算!
後來,蘇軾的另一篇文字中也透露了類似的訊息:
「⋯⋯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,急於功利,小人得乘間而入,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,後者慕之,爭先相高,而天下病矣。先帝明聖,獨覺其非,出安石金陵,天下欣然,意法必變,雖安石亦自悔恨。其去而復用也,欲稍自改,而惠卿之流,恐法變身危,持之不肯改。然先帝終疑之,遂退安石,八年不復召,而惠卿亦再逐不用。」[7]
蘇軾何以和何時得知王安石「亦自悔恨」,「欲稍自改」呢?唯一的機會就是在江寧。同時,他把王安石第二次罷相,說成完全是因為呂惠卿不想見到他「轉軚」,從中作梗而造成的,這不是說明王安石當時的意圖了嗎?王安石要起用「舊黨」中人。
王安石一定已經發覺到「新黨」班底實在不堪交託重任,不能繼續合作。他們跟已經離朝的「舊黨」精英們實在無法相提並論。不要忘記,那些因為反對新法而去職或被貶的官員中,很多都與王安石有過交流,他們的功夫底子有多深厚,他是知道的。没有了「舊黨」那些精英的支持,想把新法修改是行不通的;另一方面,若不讓新法有所改變,「舊黨」亦不會支持他,就是這樣的打算,可能會損害呂惠卿等人的既得利益,還會損害到神宗的威信。
迎回「舊黨」等人,表明當初把他們趕走的決定是錯誤得。以當時神宗的年紀,未必可以接受這種退讓。故此,在王安石致仕之後,他仍親自推行新政多年,主導權不再交給宰相,改由他自己發施號令,直接指揮。但是,在他人生最後的一段時間,好像開始了解到王安石的想法是對的。正如神宗給蘇軾的官書中所說「人材實難,不忍卒棄」。換句話說,朝中充斥着的都是一些質素不高的官員,他才會有釋放蘇軾等「舊黨」成員的舉動。可能在元豐七年左右,神宗準備好了來一次朝政大改造。只是天意弄人,他未及一試便駕崩了。還有,神宗死後,哲宗繼位,宣仁太后垂簾聽政,召回「舊黨」,遂一罷廢新法,打着的旗號就是「以母改子」。亦即是,神宗早有改變新政的打算,如今由他的母親來代他執行而已。至於是否真的像司馬光那樣極端,要把新政全盤否定,則作別論。
還有,蘇軾跟王安石見面之後的一些舉動,也可作為佐證。
首先,蘇軾是元豐七年四月離開黃州前往汝州的,期間磨蹭磨蹭,遊山玩水,還在江寧逗留了一個月,到得渡過淮河時已近歲晚了,那時候他才上表中央要求在常州定居。他似乎是有所等待。當然,他不會是(也不敢)等待神宗的死訊!我們有理由相信,他可能已收到風聲,神宗將對朝政有大動作,所以才逗留在朝廷消息流通較快的地區。
見過王安石之後,他寫信給也是反對新法的滕達道,讓他去見見王安禮,還說:「餘非面莫能盡」 [8]。甚麼事不能在信中詳談,而要「面談」那麼神秘呢?早在蘇軾離開黃州之前,他已給王安禮寫過信,約他見面,仍是那一句:「甚有事欲面話」。由此可知,王安禮是蘇王二人,甚至是「新」「舊」兩黨的聯絡人。比王安石年青十多歲的王安禮本來是不贊成兄長的新法的。不過,政治分歧只是一時間,血濃於水卻是一生一世的。没有其他人比他更適合這個任務了。要他聯絡的事大有可能就是朝中的重要政策改變。
憑着以上種種蛛絲馬跡,朱剛先生有關江寧之會的推論便很有說服力了。蘇王二人的再遇確實是一種政治上的和解。江寧之會可能就是王安石向蘇軾耳提面授,縱論分析當下的政局形勢,甚至建議他如何作好準備。
結語
曾幾何時,有中國歷史學家把一部中國通史看成是「儒法鬥爭史」,把歷史人物歸入「儒」、「法」兩大陣營之中,再加以批判。王安石被歸入「法家」,蘇軾則是「儒家」。這種分類方法不單不合乎史實,也把這兩家學說看得太簡單了。相反,把「新舊」黨爭(當然包括王安石和蘇軾的矛盾)看作是南方與北方,地主與商賈間的利益衝突,這就把範圍定得太小了 [9]。
蘇王二人本來有很多共通點:大家都是關心民間疾苦,忠心朝廷;大家也在仕途的早前階段便已發現國家在繁榮安穏的背後,隱藏着嚴重的問題;為此,大家也曾向皇帝上書求變,陳述了救國的宏圖大計 [10]。
然而,二人也有着深刻的分歧。王安石相信人定勝天,比較缺乏同理心,蘇洵批評他不近人情是對的。他經常堅持着一個宏大理論(grand theory),重視同質性(homogeneity)。蘇軾批評他「好使人同己」也是對的。王安石所堅持的理論,就是經他苦心硏究過的儒家經典,當時被稱之為「新學」或「王學」的一個體系。憑藉着這個信念,他的行事作風就是:大丈夫做大事不拘小節。可是也容易變成不擇手段 [11]。兩者只是同一個銅板的兩面。
蘇東坡是一個活潑調皮的人,不會一本通書讀到老,他支持並鼓勵多樣性(heterogeneity)。他的處事風格是「因時制宜」,就如他的文章一樣:「常行於所當行,常止於不可不止」,摸着石頭過河,無統一的理論作指導。不管是「新法」,還是「舊法」,只要是對國計民生有利的,便要「較量利害,參用所長」 [12],所以他反對「舊黨」盡罷「新政」,亦因此被後人指摘為「騎牆派」,兩面不討好。
注釋
[1] 全個職位的名稱是:「殿中丞.直.史館.判.官告院」。要完全解釋這個官銜的意義,並非此文所能及。
[2] 蘇軾《與王荆公二首》。
[3] 蘇軾《答李琮書》。
[4] 朱剛《蘇軾十講》頁229 。
[5] 蘇軾《與王荆公二首》之二。
[6] 蘇軾《次荆公韵四絕》之三,全詩云:「騎驢渺渺入荒岐,想見先生未病時。勸我試求三徑宅,從公已覺十年遲。」
[7] 蘇軾《司馬温公行狀》。
[8] 蘇軾《與滕達道六十八首》之三十八 。
[9] 劉子健(2022)《宋代中國的改革:王安石及其新政》,香港:中和出版社有限公司。
[10] 王安石向仁宗上書; 蘇軾向神宗上書。
[11] 蘇軾《答張文潛縣丞書》。
[12] 蘇軾《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》之二。
作者: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
"Unlike" 蘇東坡系列——蘇軾與王安石之三